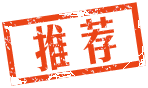喻冰四周年祭
高州蒋治泓,泣祭于景山公墓泉下亡友喻冰灵前:
什么都看见了,又什么都没有看见。青青的草原,白白的羊群,圣洁的冰山,还有清清的河水,那些红的白的黄的蓝的紫色的花,陇海线上隆隆的火车,古都西安的背影……只是没有你,有时是一个影子,立时被一阵风沙带去,什么都没有了……
冰儿,四年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的,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梦。发短信,你不回,手机也关机。直到打通家里电话,二哥才说,你已经走了,两月前。那时已是10月,南方的气候,还有些热,空气潮湿,似乎水份过多,我感到艰于呼吸,那只一头拉住往事,一头拉着我前行始终不放的手,一下子松开了,心往下沉,人还在,魂儿呢?……又过了两个月,我才告诉了莲儿。她压根不信,哭着,闹着,非得要我承认,这是假话,是骗她的,冰儿姐姐好着呢,还在拉着小提琴,奏着《冰山上的雪莲》,还在抽着雪茄,喝着咖啡,歪着头想那些永远也想不清楚的问题。
其实我倒真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不是说过吗?宇宙万物人间万象,眼见耳闻,都是假的。一切现象背后,还有一个本质。可本质在哪里,为何这般捉弄人,这一回,又象什么都是真的。生活,提供给我们的,为什么有哪么多的无常。一切虚构都消失了,一切虚构又是那样真实。
你对我说了很多的话,很多的事,我都记住,却总不明了。有时象有些明白,经你一说,我又糊涂。得知你走的一刹那,我才彻底明白,你给我的,是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思考,我哪里能想得清呢?但是,我想起你说话的眼神,那眼神告诉我,这是人生的精神大境界。这还是我在回忆你讲庄子,讲庄子扶摇九万里的高远壮阔,乘五石之瓠浮游江湖的自在超脱,庄生梦蝶的飘逸浪漫,知鱼之乐的悠然自得,等等这些话语,才让我读懂你的眼神的。
那次,我们来到祈连山牧场,你给我讲伊甸园,你说上帝来到园中,亚当和夏娃因羞于赤裸的身子,躲了起来,上帝就一声声地呼喊:“亚当,你在哪里?”
讲到这里,你看到草原上的小河边有两只白色的蝴蝶,就拉着我的衣袖,奔过去,兴奋地高喊:“治泓,快来看,梁山伯和祝英台。”说着,你打开琴盒,拿出小提琴,拉起了《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蝴蝶在琴声中翩翩起舞。我轻轻地在草尖上捉住了一只,你放下琴,拿了过去,说这就是“梁山伯”,然后在草原上疯跑起来,追逐着祝英台。边跑,嘴里边高声哼唱着《梁祝》的华彩乐段。突然,你停下来,放飞了蝴蝶,并学着耶和华老迈的步子,捏着嗓门,用苍老的声音,对着那只获得自由、正飞去寻找“祝英台”的“梁山伯”,高喊着“亚当,你在哪里?人啊,你在哪里?”声音散发在空旷的草原。
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在高而深远的蓝天白云下,我看到你的眼睛,噙满了泪水。这天,你告诉我,在阿拉伯语系中,亚当,就是人的意思。也是在这天,你告诉我,你的男朋友从德国留学回来了。还是在这天,我从那张彩色照片上,认识了你的男朋友——那个叫曹鉴的英武挺拔,气宇轩昂、学机电专业的小伙子。从那以后,二十多年来,在我情绪低落,感情沉重,孤单寂寞,生活挫折以及面对扑溯迷离的七彩世界和被病魔折腾得死去活来时,总是想起上帝“亚当,你在哪里?人啊,你在哪里!”的苍老声音。
那一年,我们去香山,上山的缆车上,你指着满山的红叶,说这个世界太美,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的分别,为什么总有一些人,让别人不一辈子牵挂都不行。要是有一个地方,没有分别,没有牵挂,就好了。二哥说,你现在去的地方,就没有分别和牵挂。二哥还说,你把分别和牵挂,带进了永恒,带进了真实。真是这样吗?冰儿。
我知道,你是一个孤独的人,心中除了女儿小冰涧,和二哥——那个为你付出一生心血的慈祥长者——之外,只有几个朋友。能够得到你的思恋和牵挂,我不知道我前生回眸了多少回,我也不知道这对于我,是凄美的痛苦,还是甜美的幸福。
你说过,一切美好的经历成为过往,都会让人心痛的。在回忆中数着日子,一切回忆都是支撑。那个西北边陲的小城招待所里,五个月的时间,为什么每次打饭,你都排在我的前面,然后回头一笑。这一笑,痛了我一生的记忆。我在我逼仄的世界,神吹海侃,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可到你跟前,我却失去了所有自信的前提。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所知道的,很多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有一回去看电影,看的是《水晶心》,回来的路上,你口里一直念着一句台词:“你可以找到一块洒满阳光的地方,那里有鸟语花香,但是没有科学。”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后来说起,你要我记住一个名字,那人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在勃鲁克堡的村庄里,进行他伟大的思考,通过对宗教的批判,以人类学代替神学。你说他最让你感动,最让你温暖的是:“不是天才的智慧创造历史,而是人类的激情。”费尔巴哈离开人世一百多年了,人们还记得他在村庄的小道上稳健的缓缓步态,还记得风中飘逸的长胡子。你还说你想不清一个事,为什么费尔巴哈这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恰恰在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死后五个月降生,同一年啊,1804。
我有太多的疑惑。我知道你正在读《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强烈批判基督教,难道宗教真那么可恶,真那么荒唐和反动吗?你歪着头,笑了,说这是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一下脸烧乎乎地起来,觉得自已太无知。你接着说,这要看时代,看语境,看民族历史,看文化人格,宗教,或许真有匡正世态,拯救人心的可能。过后,你又说,你也是很疑惑的。
你说的这些,我都是闻所未闻的。你说了,我连一丝丝儿也不懂。我也嘲笑过你是对牛弹琴,笑过后,我又是那样自卑和惶恐不安。西安分手时,你给了我一个资料,是你读哲学研究生的讲义,《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你说,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一起,是当代物理学的旗帜。里面是一系列的公式和数字,有一些中文,我一点也看不懂,也不知道你给我做什么。这个资料一直随着我,搬了几次家,很多书、很多资料都搬丢了,只是这个,还一直都在呢。可是,我还是什么也不懂,就象你在我心中,永远是一种模糊,一个淡雅的影子。只是隐约知道,你试图给我的,是一个知识王国,一个世界。
那一年的9月,星期天,你清早八晨地要我陪你进城,我不去,你告诉我,这天是你23岁的生日。我这时候才发现,你织了半年的草黄色的毛衣,已穿在身上,还新烫了头发。我们吃羊肉泡馍,到歌剧院看演出,听到“一十三省的女儿哟,就数那兰花花好”时,我掉头望了你一眼,你歪着头,会心地笑了,那澄澈得无滞无碍的眼光,在我心里嘎然惊鸿一瞥,这一瞥,让我从世俗的泥沼中走了出来,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剧院出来,去了照相馆,你穿着新毛衣,打散了头发,还是歪着头,笑着照了相。印了几张一寸的,寄回学校贴研究生证,扩印了几张四寸的,你说给你男朋友,还有二哥,有一张给我。我心里一半含酸,一半又很幸福。冰儿,这张黑白照片,已经发黄了,我一直保存得好好的,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有一回莲儿到我办公室,我给她看,她说:“姐姐年轻时好漂亮啊!”
随后我们去了嘉峪关。在公路边,你拦下一辆卡车,给了驾驶员三张香烟票,便乘坐他的车去了。我问你哪儿来的香烟票,你还是歪着头,笑而不语。登上长城,我站在城垛边上,被眼前“边陲锁钥”天下第一雄关的逶迤伟岸感动着,胸涌万丈豪情。回过头来,你泪流满面,低沉地唱着《孟姜女》:“九月里来九重阳,菊花煮酒空相望,落叶飘,秋风凉,窗前月如霜,我给亲人做衣裳……”那天是西北高原难得的好天气,太阳高悬空中,我却倏然觉得寒风凛冽,漫天雪花飘飘……我一身发冷。
后来,我们在西安火车站分别了,我送你出站时,你头也没回。我的眼前只有一个披肩长发,银灰色风衣,一手提皮箱,一手提小提琴的袅袅背影。
后来的后来,我从西北回来了,结婚,生孩子,有了安乐的小家,你着实为我高兴了很长一阵子。但是,当我把工作如何轻省,环境如何宽松舒适,家庭如何幸福等等一切,洋洋洒洒几大篇写信告诉你时,你回信却只有冷冰冰一句话:太安逸了容易出问题。不幸被你言中,以后的日子,我确实疏慵了,放弃了我曾经那么执着,那么狂热追求的理想,内心世界开始苍白起来,开始汹酒,开始打牌耍钱,开始名和利的小角逐……直到那年我生了病,成了残疾,躺在病床上,我才又慢慢咀嚼你的话,才又开始沉静下来。我还年轻,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还要活下去,所以,我还得爬起来。于是,我又站起来了。
我写信告诉你,我开始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你回信,整整四页,里面夹着几片红叶。那是一个仲秋季节艳丽黄昏,风很大,几页信纸在秋风中唰唰地响。你信中那个高兴劲儿,连同我阴暗的心境,随着秋风飘向如火的天边去。你说你去了一趟香山,走了我们当年走过的路。你在你同学的学校图书室,借到一本四川诗人胡笳的诗集《绿水红帆》,你很喜欢,看过后寄给我。
心稳手才稳,心中有力,手下才有力。这句话,是我跟二哥学二胡时,你对我说的。我的二胡到底没有学出来,这句话,却一直指点着我生活道路上的迷津,让我在人生的重重困惑中冲突出来。冰儿,在护送你的灵魂西去的路上,那些日子里,我感觉天很黑,一步一步很力巴,飘飘如欲离此世界,找不到回来的路。正是这句话,让我顿时放松起来,这才回归于这个世界,世界也才回归于我。
原以为二哥会挺不住的,可他倒来安慰我们。他给莲儿说,“那不是黑暗,而是光明,那不是虚无,而是永恒”。那些时候,二哥一直跟我和莲儿通信,怕我们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和莲儿吵架,他也劝和,总是维护着。后来,我才知道,二哥说的那句话,是雨果的《巴尔扎克葬词》,一个伟大的作家诠释另一个伟大作家,对于二哥和你,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二哥在我和莲儿心中,是一个伟大的长者。
其时,二哥已病得很重了,但他没有告诉我。信中只说左手已失去知觉,不能拉琴,连碗都不能端。后来,又说他在住院。直到小冰涧高考后录取进了大学,他才完全垮了。第二年的夏天,他也走了。我也是二哥走后很久我才得知消息,也才开始明白你和二哥的走,对于我和莲儿的意义。二哥在给我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多关心莲儿。”
我不知道哪天是你的祭日,二哥只说是8月份。我和他有语言障碍,信中也没有说明。我得到消息时是10月13号,二哥说两个月了,那就8月12日吧。
四年了。若干回梦中醒来,打开电脑,想写一段文字,可是什么也写不出。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姐姐,你是我的老师,你是痛着我也让我痛着的人。冰儿,你这一走,让我趴下,你这一走,又让我艰难地爬起来。今年7月份,我和莲儿说,该给冰儿姐姐写点什么了,可还是什么也写不出来。8月开始,写了四个月,算是说了一些话。泉下有知,你会知道我的心事。
近来心脏太成问题,心肌老是缺血,心律老是不齐,扁桃体炎和声带溃疡,又引发了心肌炎。急急喘喘中,老是想到你,大约我们相聚的日期不会远了。冰儿,悄悄地告诉你,待到我们重逢时,我一定要,紧紧地拥抱着你。
公元二0一一年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