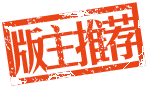|
吃新节的回忆 稻谷成熟的季节,我最爱到乡野散步。看着那黄澄澄的稻穗铺满原野,山间平地里绣出的那一张张金黄丰收的画卷,身体沐浴在那清新而悠远的淡淡的稻谷香里的时候,关于家乡的吃新节的记忆就会在我的脑海中呈现,挥之不去。 我的家乡是一个落后的山村,那里经常吃不饱饭,因而,老家的人们对稻米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老人们说,吃得伤的山珍,吃不腻的米饭。每到稻谷成熟的季节,家家户户都要摘上几串稻穗,拿回家过一个吃新节。 吃新,就是第一次吃新米饭的意思,是我家乡的人们表达对稻米特殊的感情的活动。它虽然不如除夕春节那般隆重,也不似端午中秋那般喜庆,但在我的印象里,内心的虔诚、节日的神圣,竟一点儿也不亚于除夕前对祖先的祭祀。 五月的夜空,响起几阵隆隆的雷声,妈妈就会告诉我们,这不是雷,这叫做谷炮,是上天在帮助秧苗拔节抽穗。我不知道这所谓的谷炮和雷声有什么区别,然而奇怪的是,我第二天在稻田里采割猪草时,总会看见那漫野苍翠的秧苗的上部的的确确胀大了不少,像一个孕育着小生命的妇女。出于好奇,我抽出了一根,剥开了看时,只见里面静静地蜷缩着一支尚未抽穗的稻谷,像一个熟睡的婴孩,白白的,嫩嫩的,特别可爱。于是,我把这个惊奇的发现告诉了母亲,却换来了她严厉的责备: “这是稻谷!吃新之前怎么能够乱碰!会被雷打的!” 我傻傻地站在那里,头脑中幻想出那耀眼的闪电在我的窗外闪现,可怕的炸雷在我的耳边震响,我便一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细数着日子,期盼着吃新节早日到来。 我从初夏等到了盛夏,再从盛夏等到了秋天,看着那秧苗分节、抽穗、扬花,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一些稻谷黄了,便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 “爸爸爸爸,谷子黄了,可以吃新了!” 谁知父亲却说:“要全部黄了才叫成熟呢,那时才能吃新!” 于是,我在失望之余,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眼看着这稻田从青衣逐渐换上了黄衫,还没有等到稻子全部成熟,有一天,父亲赶集买回来一块肉,大声地说:“去摘把稻谷来,今天吃新了!” “不是说吃新以前不能碰稻谷吗?”我问。 “今天吃新,当然就可以碰了。”父亲说。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奔向稻田,采了一大把黄澄澄的稻谷,拿回家里。父亲很小心地剥出一些稻米,蒸了小小的一碗,还在中间插上了一把筷子,说是一会儿吃新的时候,神仙们会用得上的。 一会儿,新米饭蒸好了,肉也煮熟了。我们就开始了烦琐而真诚的吃新节的仪式。父亲把肉装在一个饭碗里,连同刚刚蒸好的米饭一起,放在院子里的板凳上,燃烧了几片纸钱,向着门前的天空,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一边磕一边大声地说:“感谢老天爷风调雨顺,今年又得到新米饭吃了!” 接下来,还要祭祀“家神”。所谓的“家神”,就是我们的死去的老祖先。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每家人的堂屋里面正对大门的墙壁上,都会做一个简易的神龛,上面一块正方形的木板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灵位,而在两侧,则是本家逝去的祖先的名讳。祭祀家神,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祖先和我们一起共享劳动的成果和上天的恩赐。 祭祀完毕,全家人就围坐在一起,开始共同享用这碗象征着丰收的米饭。第一口,敬天。第二口,敬地。第三口,敬狗。为什么要敬狗呢?奶奶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儿是没有稻谷的。有一年,遇上了大洪灾,淹死了很多人,粮食当然颗粒无收,就连一粒种子也没法找到。就在人们绝望的时候,有人在退去了洪水的河滩上发现了一只死去的狗。这是这次洪灾里唯一淹死的狗。这只可怜的小狗浑身上下除了尾巴以外全都湿漉漉的。人们在埋葬这条小狗的时候,从它那蓬松的尾巴毛里发现了几粒稻谷。这时,村里的人们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这只小狗是为了保护这几粒珍贵的种子才遭此横祸。于是,祖先们厚葬了这只狗,还给它立了碑。至于石碑在哪里,奶奶没有说,她也无从去说,只能把这个代代相传的故事讲给我听,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只狗的恩德。 敬完了这三口,就该轮到我们吃新了。辈分的高低和年龄的长幼,都是决定吃新顺序的主要标准。如果家里有人不在,那得由长辈或者兄长代替他吃;如果他在这个家庭里辈分最高,那大家得像敬天地一样敬他一口。吃过了新米饭,庄户人家才能够到田里收割属于自己的庄稼…… 一年一年,吃新的传统渐渐简化,可吃新的记忆必将久远。我希望在稻子成熟的季节,采回几串稻穗,回味一下家乡新米饭那淡淡的清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