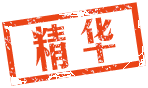那一年我是十二岁还是十三岁,已经不很记得了。只记得闹起了文革,学校的墙壁几乎没有一丝缝隙地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的课程表亦被学生乱扔的黄泥巴或者废纸砣砣和老师们群情激昂慷慨陈词的大辩论全面打乱,于是乎在没有惯例的情况下学校停课了。这种停课带来的不规则又无法确定期限但已经比几个暑假寒假之和还要长的无法命名的假期,让父母心忧,却让孩子们欣喜。而欣喜的感觉之于我,却象夏日里稀罕的凉风那样很快就吹过去了。凉风之后夏日炎炎重新来到,更觉暑气蒸逼。学校虽然不用去了,但妈妈每天安排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甚或到九也许是十的家务活让我毫无章法的忙得晕头转向乱七八糟。洗衣洗菜做饭挑水扫地打酱油买盐巴带弟弟妹妹,这些日常琐事对于今天被父母疼爱有加的独生子女们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可能也是无法承担的,但当时作为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大姐,作为父亲在外地上班妈妈常年生病并且经常晚上都在加班的一个大女儿,这些一件又一件接踵而来的家庭任务却是我必须接受不得不接受的。似乎很庄重的义不容辞。象《红灯记》里面李玉和被捕后的李铁梅应该挑八百斤那样,我几乎可以说也挑上了七百九十九斤。从早上在床上被妈妈喊醒或者被揪耳朵揪醒到晚上上床睡觉,白天忙得没有几分钟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我幼小的肩膀和双手被妈妈夸张而毫不留情的安排使用到了几乎是极限。我幼稚的头脑满满地充斥着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本应尚存的几丝童年的乐趣和即将步入少女时代的新奇好像在我的感官之外,用“我晕”、“我汗”这些今天流行的网络语言已经丝毫不足以形容我当时幼稚心灵情绪的点滴了。
在忙里偷闲的时候,我开始怀念上课的日子。就像原来总是盼望下课铃声响起来一样,我也好想上课铃声响起来。虽然不喜欢呆板地姿势不动地在老师目光的管教下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也不喜欢毫无趣味如同嚼腊的地理课自然课,但我还是想上学。想上学是想读书想看书。我一向爱看书,当然全部是小说。我三四年级开始已经看了好多小说书童话书,从连环画到大部头的文字书,我无所不爱。小说和童话书比起语文和算术书来,内容像甜美的糕点水果和喷香的米饭一样让饥饿的我馋涎欲滴,让我充满想象和憧憬的愉悦感和幸福感。而文革的开始让我这一点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不多的精神幸福转眼成为了奢侈,成为了回忆中的过往。除了领袖著作科技书籍和几部革命小说外,扫四旧几乎横扫了其他所有书籍。除了我们家里仅有的两本《红岩》《平原枪声》外,我再也看不到我喜爱的书的踪影了,小说成了小说中的小说,童话成了童话中的童话。
我突然被医生诊断出得了肺结核。生病对于我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觉得自己和往常没有两样,不发烧不咳嗽饮食如常睡觉如常。但平日里本来由我百分之九十九全权负责的家务活却明显又悄然的发生了变化。妈妈对我的事情安排忽然少多了,除了她自己勉为其难亲力亲为主要部分之外,其他一些诸如扫地抹桌子洗碗之类的细微事情则分摊给了我的大弟弟和妹妹。妈妈在安排弟弟妹妹干活时还总没忘了捎上一句,你姐姐病了,让她多休息!
这让我很感动。也让我有了空闲。从未有过的空闲使我有功夫把家里那两本书也就是《红岩》和《平原枪声》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翻来复去看了一遍又一遍,几近眼熟能详,直至书页边缘被翻得发卷发毛。那些人物和故事情节在我头脑里按照作者编定的程序反复反复又反复地巡回好多遍之后,我终于感到了一种累。其实不应说是累,确切说是一种失望。失望为什么书就那样结束了,为什么作者不将故事写得更长一点,印刷厂为什么不把书印得更厚一点,那怕是附加上一个小故事也好。失望的我只有静静而无可奈何的不想专注又不得不专注的养我所谓的病。脸色红润却精神恹恹,好像真生了大病。
这时候我父亲回来了。常年在外地农村工作一年中难得让我们见上几次面的父亲不是回来休息的,是回来写材料的。他带回了一摞麻线捆着的稿笺纸,那上面写满了他所在的四清工作队(记忆中好像是)收集的基本情况,而他这次回家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基本情况整理出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写成工作总结,然后呈交给上级领导。
写作是件艰苦的事。父亲在教导我怎样写作文时曾对我说,写文章要做到古人说的那样,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只有做到那样了,才能写出好文章。虽然当时的我对那两句诗尽管父亲再三解释还是似懂非懂,但我知道父亲说的当然是对的。王国维《人间词话》亦说到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先生说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国维先生的话如果泛指文学和艺术创作,我想他的意思也许是说只有写出千古流芳的作品的大家才能经历上述三种境界。我今生今世是绝不可能写出什么传世之作的。这一点我有百分之两百的自知之明。所以我想我是不会经历国维先生所说的三种境界的。但仅读读那几句看似简简单单实则内容万千如同一幅幅色调润泽风景各异人物丰满形象鲜明的画面的古词,我已经对创作的辛苦略见一斑了。
父亲也如我一样是永远写不出什么传世作品之类的。这一点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盖棺,却是已经论定了。父亲与文学创作今生无缘。父亲的钢笔或毛笔与有横格方格的稿笺纸或者没有横格方格的白纸接触的结果基本都是单位上的公文类文字材料,或者是写给妻子儿女的信。公文类材料程式化固定化,可以说是通俗的八股。但要往这些程式固定的八股里面装进每次都必须翻新的内容,却亦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情。
那几天我就看到了父亲在煞费苦心。父亲衣带渐宽,为伊憔悴,却似乎众里寻她千百度也不见伊人回首,望断天涯还是始终找不到路。父亲绞尽脑汁,稿笺纸上写几行又撕掉一张,撕掉一张又重新写几行,接着又撕掉一张,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头绪。万事开头难。父亲就难在文章的开头上了。那几天天气非常炎热,用大人们的话说,是伏天头。那时还没有电扇更不用说空调。屋外的太阳火辣辣的炫耀着它过度的热情和热度,屋内比外面相差无几的温度也烘热灼人。这饼不用贴在锅里烙搁在地上也似乎能烤熟的高温天气完全是一块火红的烙铁,烫死了父亲本来就几近阻滞不通的思路,又如放大镜一样成倍地放大了父亲的焦燥。父亲写两个字又赶快拿起竹扇扇几下,很快又脱下汗衫拧着汗衫上的汗水,马上又用冷水用劲的洗脸搓背。三十六计用了三十五计,父亲依然汗如雨下,热得烦燥,烦燥得做事很不顺畅,很不顺畅于是更加烦燥。
父亲终于用力丢下左手的扇子右手的钢笔,恨恨地说,这个狗日的天气没得办法做事的!硬是热得来心头慌!
父亲一边骂着老天一边在屋里来回走了几圈,又自言自语的说,怕是要换个凉快的地方写了,要不然到时交不了差。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带着他写材料那一摊行头出去了,直到吃中午饭才回来,吃完饭马上又戴上草帽出去了。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又回来了。却是满载而出空手而回,不见了早上带出去的那些材料。不过出去了一天的父亲看起来不是那么热了,也好像平静了许多。妈妈问父亲,你甩手甩脚的回来,写得如何了嘛?父亲说嗯还好还好。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悄悄问我说,跟不跟我去一个地方嘛?保证你高兴!父亲说完嘴巴一抿,嘴角带了一丝神秘的笑容。父亲没有说要带我去什么地方,我也不敢多问,只好揣着一串问号不明所以地跟在了父亲后面,一直随着父亲往前走。
一走走到了公园里。我有些莫名其妙了。莫非昨天父亲是在公园里写的材料?那么他的材料呢?父亲可是昨天空着手回家今天空着手出门的呀。我忍不住问父亲,到底去哪里嘛?父亲说你慌啥子嘛,小点声,还有几步石梯子马上就到了。
走上石梯子,穿过竹林掩映的小径,走到公园人迹罕至的僻静处,我看到了树木丛中图书馆的招牌。原来父亲是要带我到县图书馆。
我觉得我的心要跳出来了。这真是知女莫若父,知我者,父亲也。
但是,图书馆能进得去吗?图书馆的门窗上几个月前就已经被贴了封条,不许任何人越雷池一步的。里面封存了从全县收交上来的很多“四旧”书籍。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我好多次来到因为封存而无人问津的图书馆满布灰尘的玻璃窗外心怀鬼胎的左望右望暗暗徘徊,恨不得敲碎玻璃窗翻进里面去看个够,恨不得自己是孙猴子能够七十二变,好变身进去一览无遗。可是无论我怎么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终究是乌托邦。无论我如何千呼万唤,那些书终究出不来还是出不来。我只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那一幕情景真是心中苍苍,尘雾蒙窗,空看伊人,在窗一方。任凭我如孙悟空一样抓耳挠腮,心里抓狂,还是千般万般无奈,看着图书馆里的图书如明珠蒙尘埃灵芝掩蒿莱,美人弃世,却束手无策。
其实图书馆没有封存前我是那里的常客。每天一放学,我总是一路小跑到那里,一目十行跑马观花地看上几本连环画后然后又余兴未尽的跑回家。这样来去匆匆不但是因为妈妈总要求我按时回家,还因为作为老大应该承担的那一摊子总也做不完的家务事。大人们千人砾金众口一辞总说什么出林笋子先遭难,老大就该比老二老三老四要多干点活。我心中虽然一直忿忿,却也迫不得已。谁让我此生不辰,懞懵之中偏偏成了那一根倒霉的先出林的笋子呢?
连环画看多了,我开始要想看文字书。不过那是要有借书证的,可不象看连环画那样简单可以随便翻翻。寒暑假空闲多了些的时候,有一次我曾尝试着走到和我差不多高的借文字书的柜台前,怯怯地向那个埋着头写着什么满头白发的管理员嗫嚅说想办一张借书证。他抬头瞄了一下我的身高,马上就毫不犹豫的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公事公办,他说学生办借书证必须有学生证。这是规定。而我显然没有到上初中的年龄,是绝不可能有学生证的。显而易见,在如此铁板一块的规定面前,我纵有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也只能一败涂地垂头丧气。
现在父亲却要带我进图书馆了。而且是封存了那样多书籍的图书馆。你能说出我现在的心情吗?
图书馆门前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被木条钉得死死的门窗积满了尘埃,织出了蛛网。看着这门庭寥落人气冷寂的氛围,我一阵隐约的难过。想想以前的图书馆,虽说没有宁波天一阁故宫文渊阁那样浩如烟海的图书和名扬天下的大气,只有小小的一锥之地,且馆藏羞涩书籍寥寥无几,可也是青睐者众,读者多多。而对于我来说,更是朝圣的一方宝地。曲径通幽处,书房花木深。蝉噪林逾静,鸟鸣景更幽。那时处在小路尽头树林掩映竹影摇曳中的图书馆,恰似夏夜倾泻着清朗月光桂子飘香妲娥轻舞的月宫,是那么恬静而安详,清幽而绝俗,实乃远离尘嚣隔绝红尘的一方净土。那些大小小老老少少的读者们在馆内的书桌前安安静静看书的样子,那些惟恐妨碍别人而轻得不能再轻的脚步声,还有窗外时而沙沙的竹叶声时而清宛的鸟啼时而悠长的蝉鸣,是多么静谧而怡人的一道道风景呵。谁料到会落到如今秋月春风暮去朝来颜色已故的境地。
父亲带着我绕过大门,沿着墙根,来到了图书馆后院的小门。后院里栽种着几株硕大的黄桷兰树,纷繁的枝叶或盖着图书馆屋面的瓦背,或伸出后院的围墙,被炎夏的阳光晒得垂垂冉冉。正值花开季节,空气里一丝丝甜润润的花香,沁人心脾。父亲掏出钥匙,打开小门,和我一前一后走进了图书馆的后院。黄桷兰的香气更浓了,亦更甜了,而因为树木浓荫遮蔽,后院多是湿漉漉的青苔,空气也瞬间凉润了下来。
父亲的话多了起来。他一路走着说着。说是图书馆新进了一个管理员是他同事的爱人,父亲向她私下借了钥匙,才得已到这个世外桃源般的荫凉地方来写材料的。父亲说同事的爱人借钥匙给他时再三叮嘱,不要让外人知道,不要带外人进来。一定要注意影响。所以你今天来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要不明天我就不带你再来了!父亲又说本来还想带二娃三妹来的,但想想还是算了。因为人来多了闹得没法写东西,恐怕他们倒懂事不懂事的还会把人家的图书撕烂了。末了父亲又说还是人熟好办事,朝内有人好做官呵,要是没有熟人,咋个能够轻易进到这图书馆来,还能在里面安安心心的写材料呵。
走在父亲身后的我没露声色,但心中除了欣喜就是自豪。因为能够独享父亲这份信任和宠爱。我更为父亲感到自豪。他真有本事,能够带我进入这禁锢之地!。虽然这种进入有点像游击队潜入敌占区一样,必须行动隐秘,还带有那么一丝危险性(我指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一点)。但毕竟这不是张三李四王麻子随便哪个人就能够办到的。我感到有点不是一般的刺激。
而更大的刺激和欣喜马上就来了。一走进图书馆的侧门,进了阅览室大厅,我马上看见了那一垛垛用绳子梱扎着一层层码放着的几大堆书籍。如果说原来书籍稀少的图书馆是一位伶仃的少女,现在她就已经成了一位体态臃肿的肥胖妇人。那些重重叠叠叠叠重重摩肩接踵的书堆已经快要顶上图书馆不高的天花板。虽说还没有出则汗牛马,但确乎已经处则充栋宇了。从十六开的画报三十二开的文字书到六十四开的连环画,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中国的彩色的黑白的新的旧的厚的薄的大人们看的小孩们读的,真是应有尽有。我象进入了一个美梦,变成阿里巴巴进了强盗的山洞,眼前满是珠宝璀璨发光,琳琅满目。我从一堆书走到另一堆书,摸摸这本看看那本,却不知道究竟该先看哪一本。好似一个饿了七七四十九天的乞丐,突然面对满桌子的美味佳肴,尽管饥肠辘辘,却老虎吃天无从下手。
父亲在平日里图书管理员给读者们办理借书的那张办公桌前坐下,开始写他的材料。看到我这里翻翻那里碰碰,正在摸一本《古文观止》,就说你看哪本就看哪本嘛。不要每捆书都给人家解散了。记得看完给人家放好捆好。不要给别个弄乱了。——先看你看得懂的嘛,那些古文书你看得懂啥子?还有厚很了的书你几天看得完吗?看得个倒长不落(短)的你以后还会心欠欠的。
父亲几句话指点迷津,让我陡然开窍。我赶快解开一梱连环画,拿了一本就坐在地上看起来。
我看的这本连环画叫《神灯》,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说的是一个叫阿拉亭(我记得那本连环画上是这个名字)的年轻人如何得到了一盏神灯,又如何失而复得的故事。我很快被吸引住了。看到那个有魔力的巨人卑躬屈膝地对阿拉亭说,“主人,你有何吩咐”时,我对阿拉亭简直羡慕极了。我也神往有那么一盏神灯。如果真有了神灯,我就会叫那个巨人把这许多书一本不剩不为人知的全部搬到我们家里去,虽然我们家完全没有这样的容纳能力。或者吩咐那个巨人把这许多书搬到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里,在我想看时带我飞到那里一个人悄悄的看,慢慢的看。看到公主的女仆被巫师骗走了神灯,我一阵紧张一阵心疼又一阵惋惜。看到后来阿拉亭和公主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才如释重负,终于松了一口气。
室内很静。静得只听见我翻书页的声音和父亲写字的沙沙声,还有墙上大挂钟的滴答声。我不断的翻了一页又一页,看完一本又一本,恨不得把这些书一口气全看完,全吃到肚子里。听到我翻得很快的声音,父亲抬起头说,你看书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枣吗?贪多嚼不烂。跑马观花你看了学得到个啥子?
我不太甘心地稍微放慢了点速度。
正看得入神,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高亢响亮的汽笛声。是县城河对岸二铁厂拉响的汽笛。每天早上上班中午十二点吃午饭和下午六点下班的时候,二铁厂都会响起这种声音。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没有表百分之九十九的家庭都没有钟的年代,二铁厂的汽笛声就是全县城的钟表,全县城的作息时间表。父亲听到汽笛声,看了一眼墙上的大挂钟,说该回家吃饭了。
匆匆吃完午饭,父亲和我一人戴一笠草帽,顶着太阳又赶忙来到了我们的秘密阵地。父亲走得很热,在后院歇了一口气,取下草帽当扇子扇了几下,就赶快坐下赶他的材料。我也是一脸的汗水,不过管他三七二十一,我撩起汗衫擦了擦汗水,就三步并做两步窜进阅览室里,如驼鸟钻沙堆般一头钻进书堆里。
我又看了好多本连环画,多是神话童话故事。《马兰花》、《田螺姑娘》、《长发妹》、《七色花》,这些歌颂勤劳善良的神奇故事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些梗概。马兰花,马兰花,勤劳的人儿要回家。这动人的歌谣好多年后还在我耳边余音绕梁。而长发妹为了乡亲得罪山神把泉眼告诉干旱的全村人而牺牲自己变成石头的壮举,更是令人高山仰止。我十万分的为长发妹惋惜。妈妈不是经常说好人有好报吗?为什么那么善良的长发妹却没有好的归宿。过去的人们不是都信神信佛吗?山神也是神,为什么不保佑善良的人。
窗外不时传来鸟儿在竹林里的扑腾声和几声鸣叫。时而又是一声声悠长而慵懒的蝉鸣。鸟儿蝉儿协奏出一支和谐又温柔凉爽又惬意的曲子,化成了一缕柔柔细细的风,带我飞进了一本本书里那引人入胜的故事中。我的身体变得那样轻灵,好像一片轻轻的羽毛,在浩瀚无际的天宇上飘,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飘,在朝霞绚丽的晨光里飘,在星月皎洁的夜空里飘。我飞到了崇山峻岭的深林中,站在了英俊的马郎身旁,清晰的看见了他手中高高举着闪闪发光的神奇的马兰花。我又飞到了炊烟袅袅的田螺姑娘的家里,看着她环佩玎铛,轻挽罗袖为她所爱的人煮饭做菜。她是那样的美丽呵,真是素若春梅绽雪,洁若秋菊被霜。我甚至还飞到了已经幻化成石头的长发妹身旁,轻轻地触摸了她如瀑布一样长的秀发,和她已经没有生命却灵魂永存的冰冷的身体。冲刷着她身体的泉水是那么清洌,好凉好凉。而最后在一片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奇花异草面前,我看到了那朵七色花,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每一瓣花瓣都象一粒绝世无双的钻石一般,绚丽无比,璀璨发光。
“呜——”,汽笛声又响了。这是六点钟下班的汽笛声。转眼之间,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汽笛声音响而复止,止而复响中,短短的三天过去了。
已经是第四天的下午了。父亲的材料已经接近尾声,上午开始清稿,现在正在誊写最后几页了。我知道无论我怎么难舍怎么眷恋,好日子也只有这天下午这仅剩的一点时间了。墙上的大钟已指向三点过五分,那分针秒针还在没有知觉不知疲倦的向前滴滴答答。我真希望时间老人出现在我面前,那样我就可以扯住他长袍的衣袖,让他把时间暂时停留在这天下午。虽然我知道这只是根本不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想到就要离别这许多心爱的书籍,我的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难舍,难离,贪恋,希冀;陏闷,烦躁,忐忑,惴惴。时间离下午六点越来越近,越来越短暂,本应抓紧时间多看几页,我却再也没有心思看下去。我心里出现了一只小猫,在用它的细爪轻轻的抓挠我的情绪。又出现了一只兔子,上下蹦迪般的扑腾着我的想法。渐渐的一只小猫变成了几只小猫,一只兔子成了好多只兔子。我神思昏昏,心绪烦乱,七上八下,坐立不安。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是想要做什么。
这时父亲已经誊写完他的材料。他把钢笔插进笔帽里,将写完的材料装到一只大的公文袋里,然后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说,嗯,谢天谢地,终于完成了。又说,这几天我都好想拿一本书来看,但是要赶材料,没有时间。这下可以看一眼了。父亲走到一个书堆前看了看,挑了一本不太厚好像是唐宋诗词什么的,说我到外面林林头翻一下,呼吸点新鲜空气。
看到父亲拿着书走出侧门,我心里的头绪一下理清了。我一下明白了我之前究竟在想什么究竟想要做什么。父亲拿着书走到外面的姿势点石成金,给我一个提醒或者说是一个示范。我其实一直在想把这阅览室的书拿到外面,拿到不属于图书馆的任何地方,脱离图书馆的属地管辖。这仅仅是第一步。我内心深处最最隐秘不可示人的想法是想要偷偷的揣两本书回家。我是非常非常想要拿两本回家。其实从第一天随父亲走进图书馆时起,我的潜意识里就已经在觊觎这些书了。只是急于满足眼睛的饥渴,我才暂时没有意识到心底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欲望。我明白这每一本书根本不属于我,但我希望这每一本书都属于我。如果不能全部,那么部分也好。如果部分也不行,那么退而求其次,三本两本也好。三本两本都不行的话,那么退而求其次再次,一本也行。想想这么多书被人如扔敝屣地乱堆乱放在这里面,如落红飞絮红消香断无人问津,无异于明珠暗投,煮鹤焚琴,暴殄天物,岂不冤哉枉哉惜哉痛哉。再说肯定又没有人登记造册,少了几本十来本有谁知道。更何况一本两本,那不过海中之一粟,九牛之一毛。女为悦已者容,士为知己者死。书亦理应为爱书者阅,为爱书者藏。爱书的人顺手牵羊拿两本不属于自己的书,不过书生意气,雅闻逸事,无伤大雅,与市井之流翻墙入室的梁上君子不可等同视之,同日而语。孔乙己不是也说过窃书不算偷么?
我为自己行将实施的顺手牵羊罗织了一连串一点也不理直气壮丝毫也立不住脚的理由,虽然明知这些理由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但一定要有这些理由作为铺垫。否则我就师出无名。就象川戏里演的那些八府巡按出巡时必须要有衙伇们在前面鸣锣开道以示威风一样,我也需要这些理由成为我出师的衙役为我鸣锣开道。不过不是为了威风,而是为了壮胆。我外不强且中干,色不厉而内荏,气不壮如牛,胆却小如鼠。如果没有这些铺垫这些衙役,我就会空有贼心,缺乏贼胆,永远停留在纸上谈兵,坐而论道。
现在父亲出去了。父亲出去看书会有一个时间段的空隙让我可以一个人呆在阅览室的大厅里,一个人呆在大厅里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而不可失者,时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天助东风,不可犹豫。我赶快抓起两本连环画。但我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汗衫和短裤,我把书放在哪里呢。我想如果父亲是在冬天里带我来这里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把书藏在任何一个衣兜里了。厚厚的衣服一定会象抗日时期掩护游击队员打鬼子的青纱帐一样,使我拿的书有处遁形。但现在我不能想那么多了,我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最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有利的利用和转化这不利的客观条件。我撩起汗衫把书夹在裤子的腰带上,又赶紧把衣裳放下来。而薄薄的汗衫马上显出了放在裤腰上的书凹凸不平的棱角。等一下父亲进来,这毫无疑问会很快在父亲面前原形毕露。我想了一秒又马上把书取出来,放到了背后的裤腰上。我又用手摸了一摸,发现还是有些凹凸,有点凸手。我恨这可怜的裤腰真是太不争气,连小小的两本连环画也包容不下。不得已我只好取出一本,只留下一本在裤腰上。我相信这一本这小小的一本在我身上会不露痕迹。
父亲回来了。作贼心虚的我偷偷抬眼瞟了一下。只见回来的父亲将出去时带出去的那本书夹在了一张报纸里。父亲将它放在自己的公文袋上,轻轻地用手拍了两下。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长长的望了我一眼。
我的心更加虚了。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知晓了他出去的须臾之间他一向钟爱的大女儿已经做下了一件令他不愉快的事情。父亲向来爱在人前自诩自己的这个大女儿如何聪明,如何懂事。可如今这个聪明的大女儿暗地里背弃了他,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做下了一件令他今后会在人前汗颜人前羞赧的事情。看到辛苦了几天忙碌了几天的父亲,看到一向钟爱我的父亲,我明白我可能辜负了父亲对我的钟爱与信任。而比之这一点,我更惧怕父亲的脾气,惧怕父亲的雷庭之怒。父亲看起来和善,但其实骨子里的暴躁如藏龙似卧虎,这一点在他一次教训二弟时就已经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地偶露峥嵘,现出了冰山一角。
我此地无银的地摸了摸背后,有点局促,有点惶恐。
父亲自顾自走到一堆书前,抽出一本,随便翻了两下,然后又把书费力的塞回去。父亲又走到另一堆书前,同样的抽出一本书来,翻两下又塞回去。父亲再走到另一堆书前,重复了前面的动作。
我惶恐的眼神跟着父亲转。我担心父亲发现我心怀鬼胎。而父亲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反倒是我对父亲周而复始的动作疑惑起来。父亲看起来不是为了想要看书而选书,因为父亲最后是一本书也没有拿就走到他写材料的桌子前坐了下来。父亲用食指轻轻地慢慢地敲着那本用报纸夹着的放在他的公文袋上的书,神情若有所思又若无所思。父亲看起来似乎有点心神不宁。我不知父亲这是怎么了。然而比之起疑惑父亲的行为,我更担心自己。我想起父亲先前望我那长长的一眼。那一眼至少在我看来是意味深长的,那深长的意味后面好似拖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父亲可能是在窗外就已经发现了我的不轨行为,只是碍于颜面才没有当面拆穿。父亲周而复始的动作心神不宁的神态是不是一直都在等待,等待我向他坦白交待主动自首。
我现在很为自己捏一把汗。我悔不当初。我明知自己搜肠刮肚生编硬造的那些窃书的理由全部都不过是一堆雪人,任由你精心堆砌任由你造型优美还是经不住一抹阳光,却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铸下如此大错,真是十恶不赦。但是现在我实在无法向父亲坦白,我羞口难开。这不是一件令人好意思的事情,虽然面对的仅仅是父亲一人。我想悄悄的让这件事情回归原位。我偷偷把右手伸到身后,想试着小心地把书拿出来。
这时候父亲忽然一下站了起来。我吓了一大跳,马上把手缩了回来。我一下提心吊胆,手脚无措,战战兢兢,汗不敢出。父亲是不是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要当场抓我一个现行?
而父亲并没有向我走来。父亲只说了一句我出去通一下空气。就又从侧门走了出去。
我简直不知道要如何感谢父亲。父亲再次给了我一个时间段的空隙。让我有机会将事情回到开始。我赶快把腰里的那本书抽出来,放进了书堆里。
我浑身轻松下来。假设用法律标准来衡量,那么今天我是从犯罪意识犯罪动机犯罪准备再到犯罪行为,实施了整个犯罪过程。之所以没有造成犯罪后果,是父亲给了我机会。这个机会是一只温暖而有力的手,把已经走到歧途边缘的我拉了回来,让我得以犯罪中止。
父亲很快又进来了。父亲打开报纸,把那本夹在里面的书拿了出来,塞进一个书堆里,说,走,班师回朝。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突然听到隔壁的一个邻居嚷了起来,公园里在烧书了,烧那些四旧书籍,好大的火哟!
我飞一样跑到公园里。只见几大堆烈火熊熊燃烧。旁边还堆着一些尚未烧完的书籍。十多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有的用钢钎拨弄着那些火堆,有的把书一本本的扔到火堆时里。我觉得那烧的不是书而是我的头发我的皮肤我的肌肉我的身体。我全身一阵阵灼疼。焚书坑儒的史实书上看过听老人们说过,当时只觉得那种残酷惨烈愚钝蒙昧离我们离今天实在太久远。而现在虽然没有坑儒,却确乎在焚书。并且让我亲眼所见。那些被扔进火堆的书眨眼间就变成一片片的黑色纸灰变成一片片的黑蝴蝶在热浪熏腾下飘飘地飞到了火焰的上空,无声无息无助而凄怜地翻飞着挣扎着,似乎不甘心它那漂泊无定的灵魂无家可归的结局。我不知道哪一片纸灰哪一片黑蝴蝶是我的牛郎我的田螺姑娘我的七色花马兰花,但我知道他们一定都在那火焰的上空幽幽的哭诉。我唯有默默祈祝,祈祝它们幻化成一个个黑色的复仇天使,让那些使它们遭遇悲惨结局的人也遭遇同样的命运。
年复一年的过去了,我心底一直为当年没有向父亲坦白自己的过失而难以释怀。好多年后的一个夏天,也是那样炎热的的日子,我和已经退休的父亲坐在院子里纳凉。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是该坦白的时候了,我知道。我知道父亲一直在等待。我说,爸爸,你还记得当年带我到图书馆的事情吗?父亲说呵呵,记得记得。我迟疑了一下,说,我当时一直没有给你说,我差一点就从那里拿了一本书回家。我对父亲说的是拿,没有说偷。我希望父亲能够理解,能够原谅。
父亲哈哈的笑出声来。说,原来真的是两爷子(两父女),硬是气味相投啊!我当时也差点想拿一本出来。
我听了一楞。父亲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呵。我恍然明白了父亲当时那一些让我疑惑的举动。我望着父亲,不禁莞尔。
笑过之后,父亲说,我迟疑了好久,还是没有拿。
我当然知道父亲没有拿。
父亲说,你想一下嘛,人家相信你才会把钥匙给你,你倒趁人家不在的时候把东西给人家拿了,昨个说得过去嘛。再说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一个人要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都不做昧心的事情,才真正是一个君子。我们虽然只是小小老百姓,但俗话说人心动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明,这虽然是过去迷信的说法,但人还是不要做亏心事的好。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一个人做事还是要坦坦荡荡的才好。
父亲说得对。一个人做事要坦坦荡荡的才好。
毕于二0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