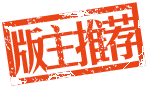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过眼烟云 于 2015-4-2 21:51 编辑
“年关”旧事 落木潇潇 “年关”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关”年年难。 “年关”,“年关”。顾名思义,“年关”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就像古时的“函谷关”、“山海关”、“嘉峪关”、“雁门关”、“剑门关”、“石门关”等一系列数不清的关口要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可能过了几千年,“年关”对于普通民众,其基本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都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只是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其过关的难易程度各不相同而已。回想起来,年都过老了,而“年关”的一些事,总是挥之不去,萦绕于心。 “爆竹”与“烟花” “爆竹三二声人间改岁,腊梅四五点大地回春”。 这是人世间沧海桑田岁月变迁多么美妙的绝唱啊! “爆竹”,火药发明之前,华夏民族用以表达重大节日之喜庆,特别是春节庆典的专用物品。其基本的方法,就是将嫩竹杆放在火上烤,让内存的水蒸汽不停的受热膨胀,拿在石头、檐坎上用力一甩,竹节瞬息破裂,发出“呯”的一声巨响。如此巡回操作,响声虽只有那么三、二声,但在宁静得有点落寞的山村,冷清中增添了几丝节日的气氛,也有了气壮山河的韵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距现在也没有过去多少年,但距“火炮”生产的年代已经有了千多年了。这里讲的“火炮”,不是旧时打仗用的“火炮”,而是重大节日用来庆典的“火炮”,相当于“爆竹”。几十年前,这个东西却是个稀罕之物。说其稀罕,其实也不稀罕。只是当时,全大队(一个村)只有一个供销点可以卖“火炮”,限量销售,价钱贵,数量少。一串“电光炮”虽只要三、二角钱,却相当于一个壮男劳动力三、四天的工分。那时,别说三、三角钱,就是五分钱,也是舅舅、姑爷之类最亲的长辈拿给我们不得了的过年钱。每到过年,我们只能买上一、二盘“电光炮”,除夕之夜隔三叉五的放两个,以表喜庆,其余不足的部分,只能靠用“爆竹”来弥补喜庆的空间了。因为,我们那里有个习俗,哪家“火炮”放得久,哪家来年的日子就红火。村庄里的人家,为了来年的日子,总是想法设法将除夕之夜的“火炮”放过通宵,但哪家哪户来年的日子仍像往年一样的不好过,甚至比往年更难过。 真正见识“爆竹”与“烟花”的热闹是在推行农村土地责任制的时候。那年,父辈们的热情,就像沉睡多年的土地,被春风微微一吹,便长出绿油油的热情与希望。正月初一刚过,男人们便开始筹划耍“龙灯”。先是“花灯”、“牛儿灯”在各个生产队隔三叉五的耍,耍到哪家糖果糕点就吃到哪家,一天要耍三、四家到七、八家不等,哪家没耍成“主人家”就会不高兴,这必竟是喜庆的事情,是耍“龙灯”的前奏,是凄惶了几十年后的喜悦。 那年正月十四,天还没黑。“凹田湾”的公场坝以及四周的菜园坝里早已是人山人海,热闹翻天。公场坝旁边的打铁房里,七、八个精壮的汉子正在大汗淋漓鼓风加火“烧铁水”,说是用来“烧龙灯”。公场坝四周的地边上,还有十几个人守候在那儿,专门负责“打油筒”(用竹子装煤油制成的照明用具来照明)和燃放自制的“烟花”。“龙灯”开始,“烟花”次第点烟,声声猛然炸响,万炮雷鸣,火花冲天,刺破长空,飘散为满天红雨,欢呼声顷刻江水汹涌。一条巨大的“黄龙”在坝子中间奔腾起来,一会儿在江水中逍遥悠走,一会儿激起海浪滔天,一会儿又腾云驾雾,“穿”“钻”“翻”“腾”态“盘”“舞”“游”“飞”姿,这根本不是“耍龙”,而是一条活脱脱的“神龙”。“火炮”是地地道道的“土炮”,“烟花”是地地道道融化的“铁水花”。负责燃放“火炮”和泼洒“铁水花”的汉子们,奋力地将自制的“土炮”不断地点燃炸向“龙灯”,将红烫烫的“铁水花”泼向“龙灯”,那“龙”,在“土炮”和“铁水花”密密麻麻的轮番轰炸下,不仅没有退缩,反而飞舞得更加疯狂势不可挡。可知道?那些耍“龙灯”的人,可是赤裸着大半个身子任凭“土炮”在身上炸“铁水”在身上烫啊!那情景,是我人生几十年再也没有见过的。我知道,那是人们在经历生活的磨难之后,抖落身上的霉气和晦气,用别样的泪水和痛楚表达对生活的喜悦和希望啊! “对联” “对联”, 就是华夏民族逢时过节,红白喜事,用来贴在门柱上用来表情达意的美好词句。 上下两句,讲究句子的排比铺陈,对仗工整,如同“天”对“地”、“地”对“空”,“大陆”对“长空”,也称“对子”。 “对子”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发展史。在新中国成立前,穷苦人家即使不识字,也要在自家的茅草房屋门柱上,贴上两张红纸绺绺,画上几个数量相等的圈圈,以表达新年的喜庆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几十年前集体生产时,再清苦和困难的人家,也忘不了在过年前买上两张大红纸写几幅对子,喜庆喜庆。村上只有一个“秀才”,人称“赵老师”。“赵老师”的父辈为人厚道喝过点“墨水”,在乡亲中有人缘。到了赵老师这里,大队和生产队便推荐其当兵,退伍后又想方设法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被公社安排到老家大队任公办教师,在我们老家那个偏远的小山村算得上响当当的“知识分子”,写对子这样的“艺术活”非他莫属,人们以请到赵老师写对子为荣。 除夕还未到,人们早早地就到赵老师家中去排队,写对子的人太多,队伍排得老长老长,写对子的人就会主动留下来,轮流帮赵老师做家务事。赵老师给乡亲们写对联很投入,词意也很美好,总是写些“岁月逢春花千树,人民可意力万顷”、“同心同德创大业,再接再厉攀新高”、“花木向阳春不老,人民跟党福无穷”、“振奋精神搞生产,下定决心干革命”、“大地寒尽春光好,农家苦去幸福甜”之类的句子。好在尽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山里人也比较纯朴,赵老师写的东西就是美好的东西,要不然像“大地寒尽春光好,农家苦去幸福甜”这样的词句就可另作他解,将赵老师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赵老师不分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写上十来天,红红的对联贴满山乡每家每户的门坊,山村家家户户飘荡着红红的希望。可年关一过,日子并没有像对联写的那样红火,家家户户又进入了每年农历二、三月青黄不接时季的“春荒”。 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后,乡村人对写对联的热情更高,赵老师写对联的表达方式有了细微的变化。如:“雄心开创千秋业,妙手绘成万年春”、“日月光华耀大地,人民伟业谱新篇”、“百花吐艳春风暖,万象更新国运昌”、“东风万里送春晖,红日高照暖人心”、大地洒雨山山翠,责任落实处处春”等,多了一分真实的春回大地的情怀。赵老师的学生们长大了,有的也成了不大不少的知识分子,写对联的事情减少了不少,再加上我又从乡村里走出来在县城参加工作,春节回家可以代师捉刀,写对联又根据每家每户的性趣讲究现说现编现写,乡亲们当着赵老师的面夸我这个学生比教师还厉害,弄得写了几十年对子的赵老师又骄傲又羞愧。为了老师那几十年在山村岁月的用真诚和真情挣来的殊荣,我总是在县城买好对联挨家挨户的送。时间稍长,别人也就不好意思找我写了,而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买上红红绿绿各式各样的对子将自己的房屋贴得光鲜亮堂,可遇上老家的红白喜事,仍然少不了赵老师那忙碌而佝偻的身影。 现在,老家山村里的很多人家都盖上漂亮的房子,逢年过节都贴上了上档次的对子,真是想要什么喜欢什么就贴什么。只是,很多人家,只有老人和小娃儿在家里,喜庆之余也有了另种凄惶。正如贴对联,年年有希望,年年也有失望。 “土火锅” “土火锅”,与锑火锅、铜火锅和过去皇家用的金火锅、银火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说其“土”,主要是指这种火锅的器皿是用泥巴烧制而成,融入了云南、贵州等地火锅和四川的特点,为川南一绝。 其基本的做法用先用少量芋头、竹笋、萝卜、海菜之类垫底,中间层加上油炸豆腐、酥肉、猪蹄、排骨之类,上面放上土鸡肉,其间加上少许老姜、花椒、盐等佐料,适当渗入温水,在锅内的烟囱内用木炭点燃,加上干干的青杠材或钢炭,细火慢炆。这是一个极其慢长又特别讲究火候的过程,中途还要不停地添汤加火,通常要二、三个小时,直熬得热气腾腾,各种肉食都快熟透香透的时候,再往火锅的最表层铺上一层精心制成的肉丸子,待肉丸煮熟,直熬得满锅香气四溢,用盐、味精、葱花调好汤味后,一锅香气冲天的火锅便可上桌了。一边吃,还可一边添材添火,加汤加菜,烫着吃,热热闹闹,极是喜庆。 川南人尤喜吃“土火锅”,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火锅的形状是圆的,一家人围着“火锅”一起吃,有团团圆圆的意思。二是边吃边加材加火加菜烫着吃,锅汤沸腾,气氛热闹。三是锅内烟道灶火熊熊,红得发亮,昭彰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不管日子过得怎样,除夕之夜每家每户都要吃“火锅”。这种吃“土火锅”的历史有多久,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只是不同的人家,“火锅”里装的东西不同罢了。听老人们讲,解放前有老两口,膝下无儿无女,年老体衰,很是凄苦。大年三十,老两口在家里炖火锅,男的说:“老婆子,您辛苦了,吃点廋的”。一会儿老婆子又说:“当家的,您牙齿不好,吃点肥的”。老两口,就这样,您帮我拈一坨,我帮您夹一筷子,相敬如宾地吃着大年三十的“火锅”,彼此温暖着对方,温暖着生活。其实,他们火锅里“肥”的是白萝卜,“廋”的是红萝卜(胡萝卜)。 我们小的时候,“火锅”也不是轻易吃得上的。大年三十,天寒地冻。父亲和母亲对我们说:“娃儿些快去找割猪草、牛草,初一天好耍。早点弄好回来,吃火锅子”。那时,我们家过年的“火锅子”,更多的时候,就是红萝卜、白萝卜、竽头加猪肉墩子。尽管火锅里没啥子东西,父亲总喜欢把火锅的火烧得熊熊的,说能把日子烧红火。最高兴,莫过于正月初几头舅舅来家耍。舅舅是城里的教书先生,一说一过笑,从不骂我们,每年春节都要给我们带礼物。舅舅来耍时,母亲烧的火锅比过年的火锅还要好,里面放了些过年都舍不得的鸡肉。我们兄弟姐妹从大年三十就时时盼,天天盼。舅舅走时,我们都舍不得,又哭又闹,扭住不放。两个妹妹为了不让舅舅走,哭得满脸鼻涕满脸泪。有一次,竟将屎尿都屙在裤子里还不放手。其实,舅舅也多想耍两天,只是当时的生活太困难,不忍心而已。这些,都是我们长大后才知道。 现在,不要说过年就是平常时候,家家户户都不缺“火锅”吃,“火锅”的做法更讲究更精致。于我们家而言,大年三十吃火锅时,更多的只有我,我的妻子和儿子陪在父母身边,兄弟姐妹都在为钱为生活而忙碌各做各的事。 看着劳苦一生两鬓斑白的父母,有时心里竟吃出了泪水。这种泪水很多家庭都流过,只是躲进了欢乐的影子。 “两家”难过一家年 真正让我感到难过的是结婚后的“年关”。 我的妻子只有两姊妹,其妹妹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地方工作,三、五年都很难回来一趟。 刚结婚那年,岳父岳母把我父母接到街上来耍,商量两家人可否在一起过年。我的父母长年在乡下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再加上过年在儿媳妇的娘家过,总感到心里有点别扭。两亲家商量来商量去,一直商量不出结果。最后,我的父母让了步,说自己的儿子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儿媳妇到婆家过年就没有人陪娘家老人了,头年三十在“后家”过,依次轮回,便匆匆忙忙的回乡下去了。 那年,我在岳父岳母家吃过年夜饭,看着老家方向的茫茫山峦,听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想起我的两个妹妹已经嫁人,按乡村的习俗是不可能回娘家过年的,年轻兄弟长年在外漂泊也不可能回家,大年三十陪伴父母的只有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心里不是滋味,竞偷偷地流了眼泪。 第二年有了儿子,轮着到我的父母家里过年了。这对我的父母来讲,真是双喜临门,高兴得不得了。父亲走了几十里山路赶到城里,也不知是从谁家借的“背带”,硬要帮我背儿子。那年,我和我的妻子、儿子在老家过了一个众星捧月的热闹年。当然,我也不知道我的妻子是否像我一样悄悄地流过眼泪,也不知道我的岳父岳母可曾暗自伤心。 自此,“年关”成了我和妻子陷入两难境地,很难选择的一个“关口”。 后来,我的岳父岳母得了重病相继去世,我和妻子在一阵痛苦之后,过年陪父母那种两难选择的苦涩慢慢地淡化了。我妻子的父母比我的父母年龄要小很多,我的父母至今都双双健在而他们却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们必竟把舍不得放手近乎“独女”的女儿交到了我的手上,真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凉。 我的儿子是独子,我未来亲家的女儿也可能是独女。他们结婚已不可能是两个儿女的婚事,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婚。这种情况,于偌大的中国,简直是比比皆是,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处理得好的,而且还要持续好几十年。 想到这里,“年关”,仍然是今后家里几十年很难过去的一道坎,令人惆怅。 经典老歌 记忆深处,最美好,最温馨,最充满希望和诗意的“年关”,当数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 那时,人们被土地的恩赐填满了肚子,填满了希望,过年就是一场丰收果实的比赛,一场走亲串友的“大联欢”。亲戚朋友之间,无论到哪家哪户,都有美味可口的食品,吃不愁,穿不愁,真是处处春意闹,方方人情浓。 那时,李谷一老师《小花》里的“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公社还有高音喇叭),总在田间地头飘曳,青涩的情愫被美妙的歌词轻轻唤醒,心中有了甜滋滋的感觉,仿佛身边已经有了美丽的姑娘。 那时,李谷一老师《在希望的田野上》中的“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十里哟荷塘十里花香”,响彻神州大地,唱得泥土芬芳。歌儿唱出了改革开放国家民族的欢腾,唱响了经济腾飞之初人们心中的欢畅。 那时,行走在田间地头,乡村小径,哪怕是见了小溪边的野花野草,我们年轻的心灵总会生出莫名的感动,禁不住在心里放声歌唱:“百灵鸟从蓝天上飞过,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年轻的心中,那种对国家昌盛民族腾飞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同龄人听着这些歌儿长大,听着这些歌儿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听着这些歌儿成家立业发奋图强,让春节过得一年比一年热闹。 也许是人的心是没有止境,也许是人生的奋斗历程没有止境,也许经济社会原本就该螺旋式的前行。 近二十年前,我最小的幺兄弟外出打工,虽没有多少文化,却靠勤劳和机灵在外面打工挣了不少钱,老家修了小洋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找的钱一年比一年多了,也做起了当老板的梦,自己办起了小工厂。开始两年賺了点钱,但慢慢的钱就不那么好賺了,为了支撑那个工厂,还欠了不少帐。 近几年,父母一天天老了,走路都显得很吃力,很想兄弟回家过年。兄弟终于回家了,父母高兴得不得了,见人就夸兄弟争气了,当上了“老板”。其实,在兄弟办厂的地方,不少企业都垮掉了,有的老板都跑了,工资都找不倒地方拿。我身边熟悉的人,也有因投资失败两口子五六十岁了还出去打工,也有因债台高筑无力偿还抛下父母抛下妻子儿女悄然“失踪”。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买房子欠了多少帐,兄弟办厂欠了多少账,兄弟更是不敢啊! 今年除夕,我和兄弟买了很多“烟花”“爆竹”,弄了很丰盛的年夜饭,陪年迈的父母开怀畅饮,想过一个着着实实的闹热年。喝着喝着,比我小七、八岁一向强势的兄弟,竞把眼泪都喝出来了,禁不住感叹:“哥啊,现在吃也吃得好,穿也穿得好,耍也耍得好,却觉得心头睹得慌啊”。 兄弟酒喝高了,喝醉了,情到真处自然伤。我生怕被父母看出点什么,赶忙对兄弟说:“好几年没给父母一起过年了,我们敞开来喝两碗。酒干了吼两首年轻时的歌”。我们从《小芳》唱到《北国之春》,从《牧丹之歌》唱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从《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到《我爱你中国》,从唱得全的到唱不全的都唱了。侄儿侄女们理会不了我们的歌,而且是这么老的歌。 那夜,我和兄弟很晚都没能入睡。醉眼迷濛,直冲云霄彩光四射的“烟花”光芒,刺破浩瀚的夜空,如我们歌儿中一只只、一串串、一片片、一群群数也数不清的“百灵鸟”,从蓝天上飞过,飞过,再飞过。 |